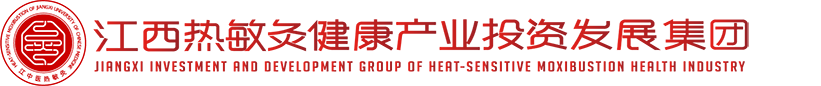
0791-85997085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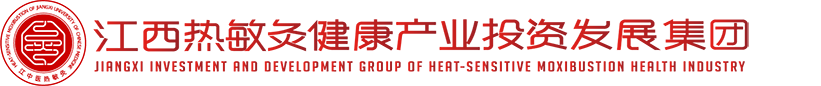
0791-85997085
地处北京前门大街的“中华老字号”长春堂药店,是一家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老药店,其名“长春”与道教渊源颇深。长春堂第一代开创者孙振兰、第三代传人孙崇善、第四代传人张子余均信奉道教。长春堂起于市井,从走方医到“连家铺”,到发展为驰名京华的大药店,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。
售丸散膏丹,从小药铺发展成大药店
清乾隆末年,京城有一位走街串巷行医卖药的走方郎中,经过多年的奔波有了一些积蓄,便在前门大街鲜鱼口胡同内的长巷头条开了一家坐西朝东的小药铺,结束了走方医的生活,此人便为山东招远来的道士孙振兰。小药铺门面不大,前店后宅,是家铺合二为一的连家铺。小药铺虽然也售卖一些家传的丸散膏丹,但以卖自制的闻药为特色。闻药由桑叶、桔梗、薄荷等中药为主,加入少量冰片、麝香,轧成极细粉末,具有芳香开窍、祛暑清火的功效。使用时,蘸上一点,吸入鼻内,一股清凉的气息沁人心脾,全身顿觉凉爽舒畅。
小药铺第二代传人孙学奎为孙振兰的儿子,子承父业,继续卖丸散膏丹和闻药,同时也不断扩展所经营的药品种类。笔者通过调查,共发现《长春堂丸散膏丹配本》《北京长春堂药目》《杂症诸方》《长春堂拣选药方》《仁一堂药目》等相关“药目”5种。从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馆藏抄本《长春堂丸散膏丹配本》(1864年)来看,长春堂的药品种类分风痰、伤寒、暑湿燥火、补虚损、脾胃泄泻、饮食气滞、痰饮咳嗽、眼目口齿、妇科、小儿、外科、遗补门等12门,载方共计391首。
到孙学奎的儿子、第三代传人孙崇善执掌经营时,小药铺开启了发展壮大之路。孙崇善,号三明,出生于同治二年(1863年)。孙三明受家传影响,在房山顾册村娘娘庙皈依了道教,做了火居道士,火居道士是指有家庭妻儿的道士。后来,孙三明在永定门外附近的公地村修建了一座小道观——长春观,经常在那里修行。公地村是现在的马家堡路东永定门外街道片区,长春观遗迹已然难寻。北京西便门外有一座著名的白云观,长春真人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东归后在此修行。白云观也是孙三明经常出入的地方。后人推测,孙三明修建长春观,并将小药铺定名为“长春堂”,或许与其仰慕丘处机有着密切关系。孙三明蓄发梳鬓,着黄冠道袍,行道礼,一边出入庙宇,一边悬壶济世。
光绪十三年(1888年),25岁的孙三明接任长春堂掌柜。彼时,长春堂所售药品“皆祖遗秘方”,包括“丸散膏丹者约百数十种”,其中仍以家传闻药最为出名。1898年,孙三明买下位于崇文区(现属东城区)兴隆街西段的一处两层楼的门面,开创了长春堂中药厂,成了创制避瘟散、无极丹,抵制日本仁丹、宝丹的有力资本。
对抗仁丹,避瘟散名扬四方
清末民初,列强纷争,中国经济凋敝,洋货充斥市场,日本的祛暑闻药“仁丹”和清凉闻药“宝丹”在中国大肆宣传和倾销。仁丹有一幅广告,一个日本人身着礼服,头戴拿破仑双角帽,翘着两撇八字胡。这幅“翘胡子”广告遍布城市大街小巷,尤其在华北地区,很多地方的墙面上粉刷着这幅图像的广告。在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等报纸上,仁丹广告也十分常见,广告宣称仁丹“东瀛第一,备急圣药”“寰球无二,常备神药”,将之打造成“没病强身、百病皆治”的万用保健药。
仁丹的配方为:甘草、阿仙药、桂皮、茴香、生姜、丁香、益智、缩砂、木香、薄荷脑、龙脑、甘茶、芳香性精油,其中只有甘茶是唯一的日本本土原料,而且甘茶只起调味作用,并非有效成分。在瘟疫多发、医疗条件差的旧中国,一方面是民众需求,一方面铺天盖地的宣传和倾销,仁丹与宝丹一起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市场。长春堂的闻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,孙三明内心也起了波澜,他怀着一争高下的决心,开始从配方到制剂改良自家的闻药。孙三明尝试在药物中加入香料,果然药香更浓,也增强了避瘟散芳香辟秽的功效。说到这里,还有一个小插曲。当时,避瘟散里加入的“香”靠大栅栏云香阁供给,一元一斤的高价给避瘟散增加了不少成本,从1914年到1924年,十年中一直维持这种状况。1924年,孙三明以五百银圆的巨款将云香阁的制香工人杨山挖来长春堂,得到了香的配方,受云香阁掣肘的问题彻底解决了。据说,避瘟散的畅销引得云香阁也仿制了一种避瘟的药物出售,但因为药品质量和影响力不足,终是昙花一现。
光加入香还是不够。孙三明还让弟子张子余会同长春堂中医师董静峰、北京田川医院的西药师蔡希良改良配方,并解决药物粉末粗糙、干燥的问题。最终,在蔡希良的帮助下加入了甘油。甘油油润黏滞,用作赋形剂还能促进药物的吸收。就这样,1914年前后,新一代闻药——避瘟散(由檀香、零陵香、白芷、香排草、姜黄、玫瑰花、甘松、丁香、木香、麝香、冰片、朱砂、薄荷冰、甘油组成)研制成功了。
1915年,为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,中国掀起了“抵制日货”运动。避瘟散应时上市,从功效、宣传上均与仁丹针锋相对。仁丹“专治伤暑中寒、水土不服、腹痛吐泻、卒中昏倒、头痛目眩、酒醉船晕”,避瘟散主治范围更广,包括“感受瘟邪,霍乱吐泻,晕车晕船,嘈杂恶心,饮酒过度,山岚瘴气,感受煤气,瘟疫杂症,偏正头痛,口舌生疮,风火牙痛,咽喉肿痛,蝎蛰虫咬”。营销上,孙三明采用了借力打力的策略。针对仁丹的商标图案,他以自己身着道袍、手持太极八卦图的形象为商标,内书“长春堂太上避瘟散”八个醒目大字。这一图像与仁丹“翘胡子”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针对仁丹的宣传语,孙三明将避瘟散宣传为“防疫居家旅行,不可不备”的防疫圣药。“抵制日货”是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,起到了一定的作用,但难以遏制日货倾销的局面。避瘟散与仁丹一直较量至抗日战争取得胜利。
避瘟散的功效优于仁丹,通过广告宣传和民众的口碑,很快就打破了仁丹独霸的场面。避瘟散销路和名气打开了,经济又实用,几个铜板就买一盒(瓶),深受民众喜爱。之后,孙三明针对宝丹,又创制了无极丹以抗衡。无极丹虽然在包括平津、河北、河南在内的北方销售盛极一时,但终未造成避瘟散那么大的声势和影响。
据长春堂的老工人王玉清说,1919年至1923年,避瘟散每年销售3~4万盒,到1924年一下子就达到了13万盒。避瘟散的成功,不但抗衡了日本的仁丹,也为长春堂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基础。长春堂从最早长巷头条小小连家铺发展到头条胡同里路西51号至57号几十间房屋的产业。长春堂建立了集采购、制药、包装、售卖为一体的经营模式,也成为与同仁堂、鹤年堂、万全堂、千芝堂齐名的京城五大药铺之一。(张立平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)
稿件来源:中国中医药网
稿件链接:http://www.cntcm.com.cn/news.html?aid=223575
责任编辑:刘君
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
